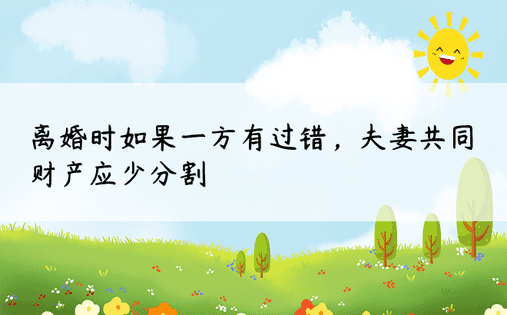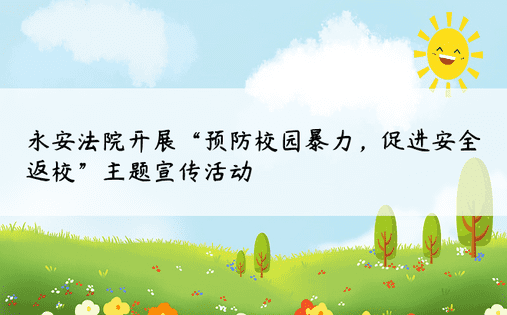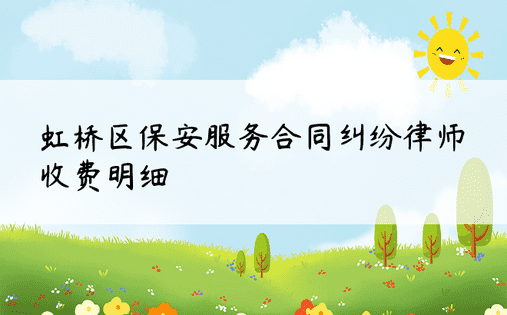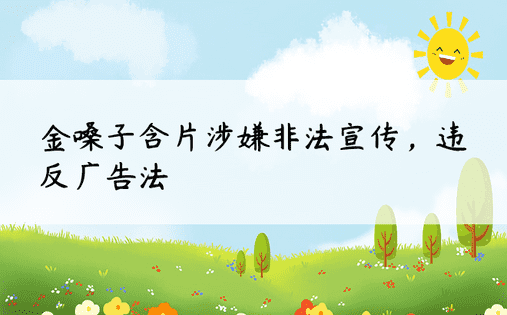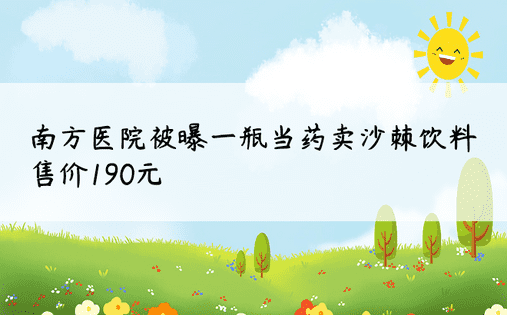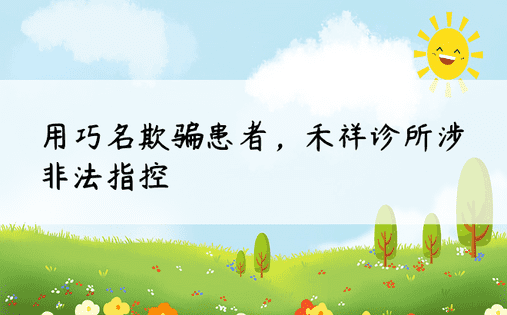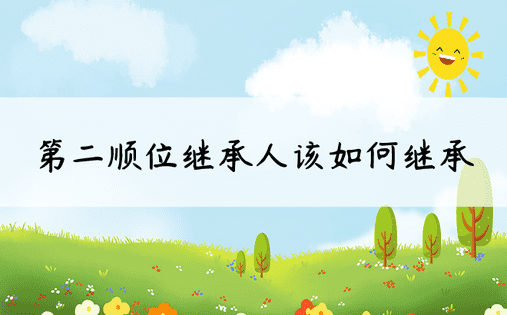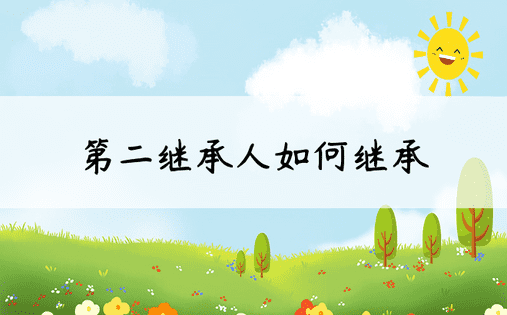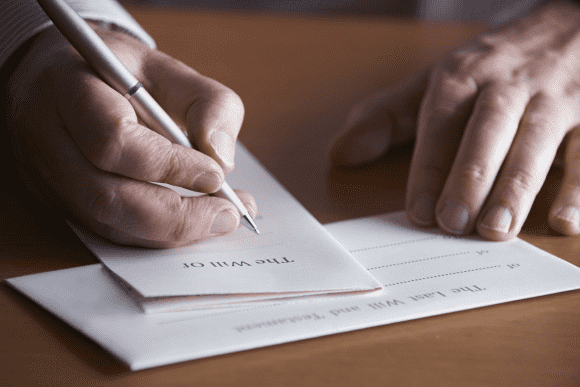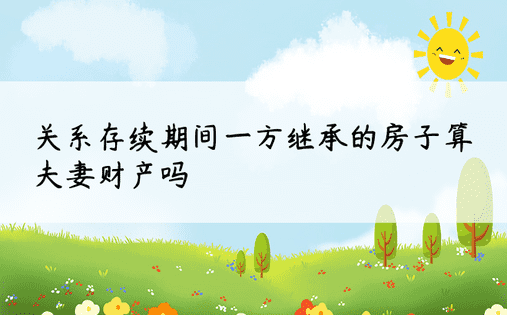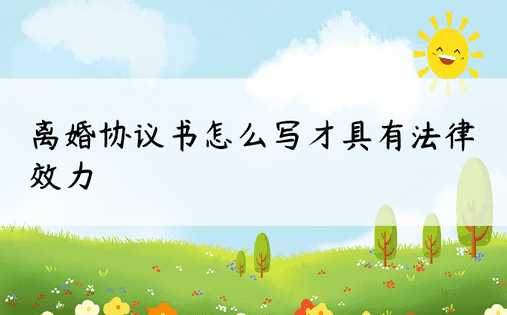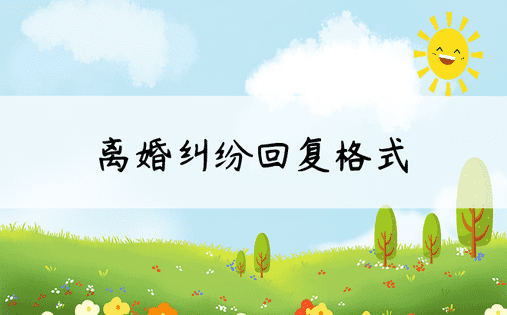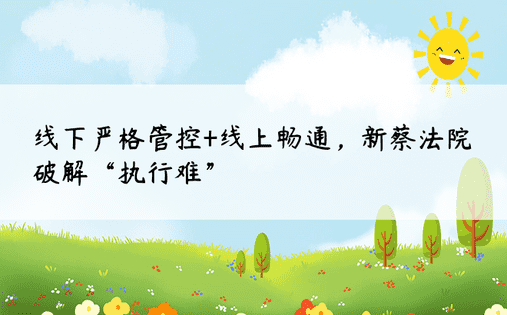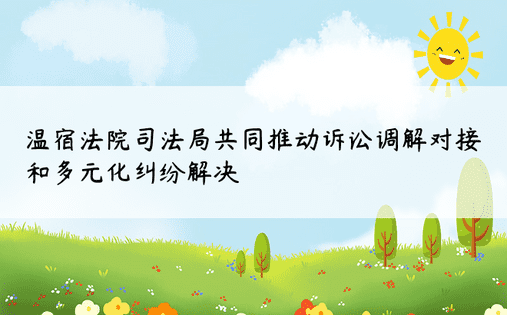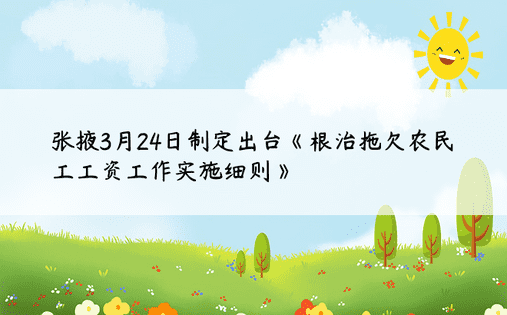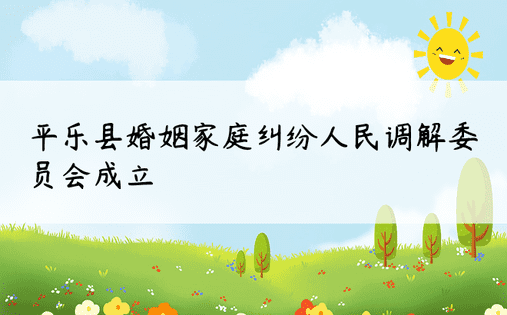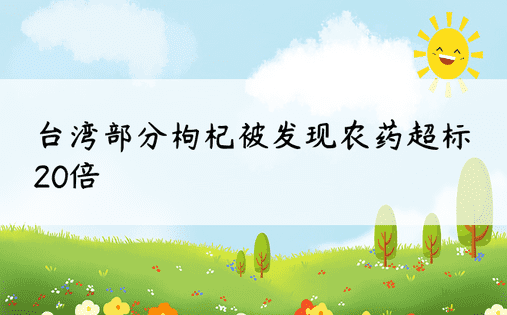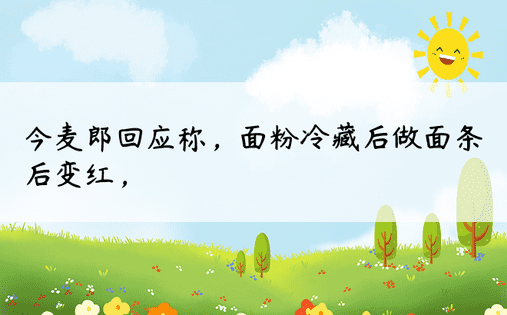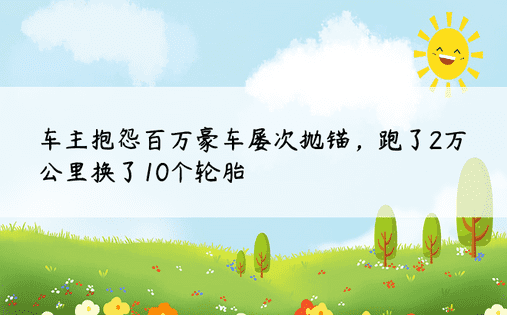(一)身份权的保护规定
私法中的身份权保护规定,首先应聚焦《民法典》中具有请求权基础地位的规范,这类规范限于两个目的范畴:一是底线救济,聚焦老、弱、妇、幼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保障;二是危机处置与退出赔(补)偿,如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此外,身份关系法上还有不直接形成请求权基础的身份关系的概括保护规定,这些规定不能指明保护内容与责任形态,但可用于结合请求权基础规范阐释权利内容与行使条件。其次,其他法律中关于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保护的相关规定,也是身份权保护的重要法源。
公法及社会法中存在比私法中更丰富的身份关系当事人保护规定,不属于《民法典》第1001条所说“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典体系宣告了身份权的私权属性。公法及社会法上保护规定只有在通过转介等方式纳入私法上请求权基础规范解释范围时,才能作为“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被考虑。
(二)身份权的确权规定
确权即通过提取权利公因式,形成原权架构,引导保护规则(救济权)建构,是权利保护规则体系化建构的前提根据。确权须基于十分确定的客体,如物权围绕物之归属与利用而确认。《民法典》第112条与第1001条所采用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表述欠缺客体语素,无法基于客体完成对权利圆满状态的公因式抽取。客体语素的缺失是身份权确权停滞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使身份与人格之间主从地位颠倒,形成现代身份权的派生性地位。因身份权在客体与内容等方面依赖于人格权等基础性权利而无法自足,故存在“身份权不构成原权”的观点。
身份权的功能是确保身份利益的正当实现,身份利益是身份权(义务)的客体,而“身份利益是派生的人格利益”。所有身份关系引发的基础性人格权益重组均可归入三种功能范式:其一,以强化身份关系中权利人自身的基础性人格利益为目的,所派生的身份权为获益性身份权;其二,以强化身份关系中他人的基础性人格利益为目的,所派生的身份权为利他性身份权;其三,以身份关系当事人互享基础性人格利益为目的,所派生的身份权为互益性身份权。
(一)获益性身份权
获益性身份权包括未成年人对其身份的知情权,未成年人获得抚养、教育与保护的权利,父母从成年子女处获得赡养、扶助和保护的权利;需要扶养的夫妻一方要求对方支付扶养费的权利;被监护人获得代理及人身、财产权益保护的权利;符合条件的成年子女、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及未成年弟妹获得扶养的权利,以及符合条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获得赡养的权利等。获益性身份权可在身份关系法中以诸如“未成年人权利”之名被确权,也可分散由身份义务、职责作用于权利人基础权益,因而由基础人格权益派生确认。
身份权保护的首要目的是维持与修复身份权派生之条件,故获益性身份权的保护规定往往限于:因不履行监护职责而撤换监护人、离婚时的扶养权及探望权的分配与行使限制,供养人违反供养义务而承担支付相关费用责任等。
(二)利他性身份权
利他性身份权是以保障他人身份利益为目的的身份权类型,包括父母履行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义务而产生的权利,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送养权,监护人履行代理、保护职责而产生的权利,由监护权衍生的夫妻离婚条件下的探望权,赡养义务人履行义务而产生的“孝老权”等等。利他性身份权的客体是保护者在替代被保护者亲自行为时的自由。法律未规定的利他性身份权对第三人的排他效力可从两方面证成:其一,被保护者的获益性身份权被第三人损害而获得基础性人格权益的排他效力,这一效力“委托”给作为保护者的利他性身份权人行使;其二,国家与社会出于对父母的信任而将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权“委托”给父母。
部分利他性身份权还以利己性人格利益为第二位客体,亲权、亲属权就比非血缘关系中的监护权更具情感自利意义。利他性身份权所包含的利己性人格利益在身份关系法上缺乏保护规定,应根据该项利益的重要性以及身份权人履职的效果与能力来确定保护范围。若欺瞒当事人对真实身份关系的知情,造成身份权人对保护职责与情感之错付亦或造成身份权人错失天伦之乐,均导致身份权人的利益损失,会引起财产与精神损害赔偿。
(三)互益性身份权
互益性身份权是通过家庭成员之间扶养关爱等利他行为,在满足自身身份利益的同时,保障他人身份利益的权利类型。其包括夫妻之间相互扶养、同居忠诚、家事代理等权利,以及为保护夫妻共同财产的撤销权、抗辩权、追认权等形成权。此外其他家庭各成员之间的互助互爱也能在较弱程度上形成互益性身份权。
夫妻共同投入维持婚姻生活所需的忠诚关爱、陪伴帮助、合作育养等人格利益,形成对所投入人格利益的共同支配与分享。夫妻各自对人格利益共同体的投入多寡,抑或遭受对方过错伤害的大小,又会积累印刻在婚姻关系中,影响各自在人格利益共同共有中潜在份额的消长,最终折算为在离婚财产分割、离婚损害赔偿、家务劳动补偿中的财产额度。配偶权有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取决于夫妻对人格利益共同共有的投入相对各自保留部分的优劣地位及其公示程度。只有夫妻真正“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配偶权客体已上升为配偶身份利益即“婚姻的圆满状态”,第三人知道或应知这一状态时,其破坏夫妻关系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对配偶权的侵害。
身份权参照人格权保护的必要性是基于身份权与人格权间的派生关系。若案涉身份权的派生基础并非人格权益,例如监护权的部分内容系由财产权派生(对被监护人财产的保护与代理权),则该权利与人格权之间因欠缺相似点而无法桥接。《民法典》生效前,司法实践以较为宽泛的路径对缺乏保护规定的身份利益予以扩张保护,对“隔代探望权”“被探望权”等存疑的身份权类推适用有名身份权、具体人格权或者其他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亦有根据案涉权利的对世性而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这种宽泛路径看似赋予了法官弥补法律不足的裁量权,实则是因身份权缺乏原权框架指引而导致的实践失范,可能导致侵权责任法挤占身份关系法对身份权确权的主导性,造成司法对判断哪些身份利益缺乏必要保护、应参照何种保护规定缺乏明确标准,妨碍身份权纠纷类案类判。
确定案涉身份权的基础人格权类型和参照对象的方法有三种:其一,参考权利人主诉利益类型判定。例如第三人侵害配偶权案件的原告因配偶通奸使自己遭受讥笑而倍感屈辱,其主诉利益焦点是名誉损失,配偶权参照对象为名誉权。其二,根据弱者利益保护需要确定。例如在夫妻生育权冲突中将女性生育权保护参照对象定为生命权、健康权及身体权。其三,兜底与有限参照一般人格权。
可资身份权参照的人格权保护方法包括《民法典》第995条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人格权请求权;第997条之人格权禁令;各具体人格权所附带的专门保护方法等。以上保护方法之间关系如下:首先,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应首先用于纠正第三人妨害身份权派生条件、破坏家庭整体价值者,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可用于探明被保护者合理容忍限度,控制亲权与监护权合理行使幅度。其次,人格权禁令可作为预防性手段参照适用,权利人应证明正在或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可能对身份权赖以派生的家庭关系条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复次,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可用于参照名誉权保护或以名誉利益为主诉点的身份权保护场合。赔礼道歉需证明加害人有过错,应契合谦和容让的家庭伦理导向,不宜裁判长辈对晚辈进行赔礼道歉。最后,身份权保护通过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5条引致精神损害赔偿的,不仅要求权利人遭受严重精神痛苦,还要求精神利益具有通过排斥第三人干涉或向身份关系相对人提出请求而维护家庭整体价值的正当性。
四、结语
身份权的派生性妨碍了立法的统一确权,引发身份权保护漏洞填补机制失范。通过回溯身份权所维护的基础人格利益,可区分为获益性身份权、利他性身份权与互利性身份权,明确各类身份权的必要内容与保护范围,并由此明确身份权优先保护与参照保护的衔接关系,澄清参照保护的必要性与技术路径。
(本文文字编辑寇涵傲。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章链接:《身份权的派生确权与参照保护》